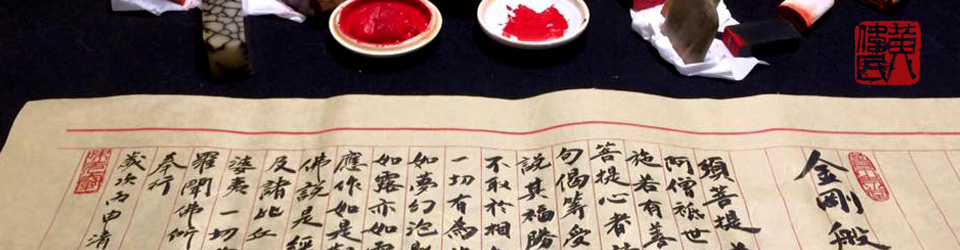![]()
黃偉民易經講堂 | 贊助 |
原稿日期:2015年11月4日
《翻論語,談政治》
傘兵散勇,殺入區議會選舉。
建制派拿出防衛金鐘罩式口號:
不談政治!
做政客,不談政治?
對,在他們心中,政治骯髒,他們做實事,不談政治。
港大校委會的閉門會議是政治;港鐵突然神勇針對學生樂器是政治;食水含鉛是政治;青馬大橋被船一撞,癱瘓機場也是政治……
政治污糟邋遢,他們做實事的人,不談政治。
很多香港人,都有這種無知的想法。
政治,是管理眾人的事。
不只做特首,才是政治;在公司做一個主管,下一個決定;搞一次舊同學敘會,時間地點消費額,便很政治;家中做節,幾個家庭,在那裡吃?吃什麼?誰付帳?從來都複雜,這也是政治。
一個家,一間公司,一個組織,一個城市,以至一個社會,一個國家,一個地球村,事事都政治,人人都複雜。
所以,古人對大政治家,大宰相有要求:
調和鼎鼐,燮理陰陽。
協調所有矛盾,令不同意見的人都滿意,安居樂業。
論語二十篇,第一篇「學而」篇,講做學問的修養;第二篇「為政」篇,說作為政治領袖的方法。
孔子認為,為政,作為一個領袖,重點不是權力,是教化。
教,是教育;化,是感化。
身處亂世,人人賣弄聰明機巧,重視權力鬥爭,社會秩序混亂,特權處處,公義不彰,文化衰敗。
孔子面對這種時代,認為為政,權力沒有用,惟有用人天生的善良德性,誠實的面對自己,作出判斷決策。
孔子哲學,認為凡事沒有偶然的。他在易經坤卦文言中說:
臣弒其君,子弒其父,非一朝一夕之故,其所由來者,漸矣。
這也是佛家所說的因果規律。
論語「為政」篇,第一章,就開宗明義的說:
子曰: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
孔子認為,作為一個政治領袖,內心有道,用人的天生善性出發,表現出來的行為,決定,就無懈可擊了。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樣,有中心思想,有政治抱負和信念,所作的決定政策,自然天下人圍繞而旋轉。
第二章,話鋒一轉,說:
子曰:詩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無邪。
說政治領袖之道,為什麼突然提到他編輯「詩經」的標準來?
孔子刪詩書,定禮樂,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那裡?
一句話,就是思無邪。
人,不能沒有思想,但思想不能走歪路。
孔子認為,一切政治問題,社會問題,只是思想問題。人只要思想正,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了。
作為政治領袖,為政的人,第一要務,就是思想不走邪路。
然後,第三章,說出為政的方法:
子曰:道之以政,齊之以刑,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,齊之以禮,有恥且格。
領導一個國家,一個社會,一個組織,一間機構,如果只用規章來領導,再用刑法來管理,民眾為了不犯法,會鑽法律的漏洞,逃避責任,然後無恥的沾沾自喜,自鳴得意,認為你奈不了他何。
但如果以道德來領導,每個人都自重自愛,再齊之以禮,以禮樂教化,大家會自動自發。錯了,有慚愧心。有恥且格,當民眾都有羞恥心,就達到政治目的了。
今日大陸人的問題,歸根究柢,就是上上下下,都沒有羞恥心。所以,全國都以動物本能來生存,社會就烏煙瘴氣了。
跟著第四章,孔子自述一生所學的進程,但這與為政,又有什麼關係呢?
子曰:吾十有五而志於學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順,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
孔子說:我十五歲時,就一心向學。因此,到了三十歲,就能確立自我。
進一步鑽研學問,到了四十歲,就擁有堅定不移的自信,對人生不會感到迷惑。
貫徹這個生活方式到五十歲,就清楚宇宙的規律法則。六十歲,就明白世事的錯綜複雜,不會偏執一方。
這樣了七十歲,意思是人生的總目標,也是一生追求的境界,即使隨心所欲的行動,但也不會超出作為一個人的社會規範。
即使率性而為,也不會對周邊的人,造成困擾。
論語的編輯,為什麼將這一章,放在這裡?
為政篇,說的是政治領袖之道。
第一章,說的是誠。對人對己坦白。
第二章,說的是正。不能邪,不用聰明機巧。
第三章,說德化,主禮治。單用刑法威嚇懲罰,達不到政治目的。
第四章,焦點在最後一句,從心所欲而不踰矩。很多人追求權力,以為有權力就可為所欲為。孔子透過他一生的學習經驗,告訴大家,人生的成功,在於從心所欲仍不踰矩。
為政篇,既然是說政治領袖的修養,就告訴大家,作為領袖,自然擁有權力,但權力是工具,是完成領袖責任的手段,不是目的。
使用權力的最高境界,是不會對別人造成困擾,完全不會做出一個人不該做的事來。
今日的社會亂局,就是為政者,背棄論語的原則,闖出的禍害來。中共又大力推揚孔子,但孔子學說,大陸官民,一概不通。
治亂之別,就在於利用孔子,招搖撞騙,還是深研孔學遺風。